? ? ? ? ?近二三十年來(lái),作為當(dāng)代中國(guó)史學(xué)的一大變化和進(jìn)步,我們整理出版了一大批由當(dāng)時(shí)在華西人攝影或創(chuàng)作、反映近代中國(guó)方方面面的圖像資料。
? ? ? 相比之下,存在“三多三少”現(xiàn)象:以歷史老照片居多,畫像所占比例不大;以問(wèn)世于民國(guó)尤其是抗戰(zhàn)時(shí)期的作品居多,涉及晚清較少;多為以揭秘自炫、以獨(dú)家圖片吸引讀者的書(shū)籍,以大歷史觀和正確歷史觀進(jìn)行深度解讀的書(shū)籍較少。因此,讀張建斌編著《〈倫敦新聞畫報(bào)〉中的中國(guó)人:1842—1912》,不禁感到眼睛一亮。
? ? ?《倫敦新聞畫報(bào)》創(chuàng)刊于1842年,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圖片新聞為主要特色、極具影響的周刊。有別于多數(shù)西人以獵奇心理隨景拍攝照片,該畫報(bào)圖文并茂,圖像為記者現(xiàn)場(chǎng)素描,配合文字進(jìn)行新聞報(bào)道,除同樣具有真實(shí)、直觀的特性外,還具體反映了記者及該刊的對(duì)華傾向、態(tài)度,具有思想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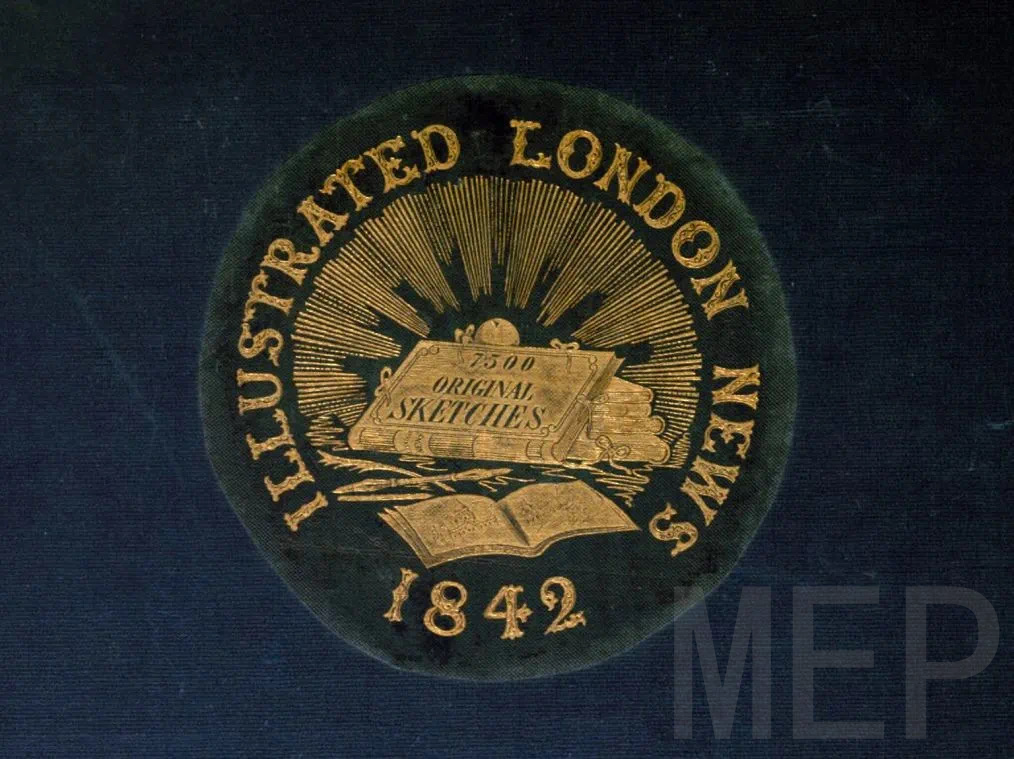
《倫敦新聞畫報(bào)》檔案卷宗第一卷
? ? ?1842年至1912年七十年間,該畫報(bào)合計(jì)刊行3696期,其中“中國(guó)”(China)一詞在文字報(bào)道中出現(xiàn)15261次(高于對(duì)俄、德、日等國(guó)的報(bào)道),畫像多達(dá)千余張。這七十年幾乎與晚清歷史重疊,張建斌一書(shū)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圖像二百余幅,以解析該畫報(bào)所“塑造”的晚清中國(guó)人形象,揭示圖像背后的歷史意蘊(yùn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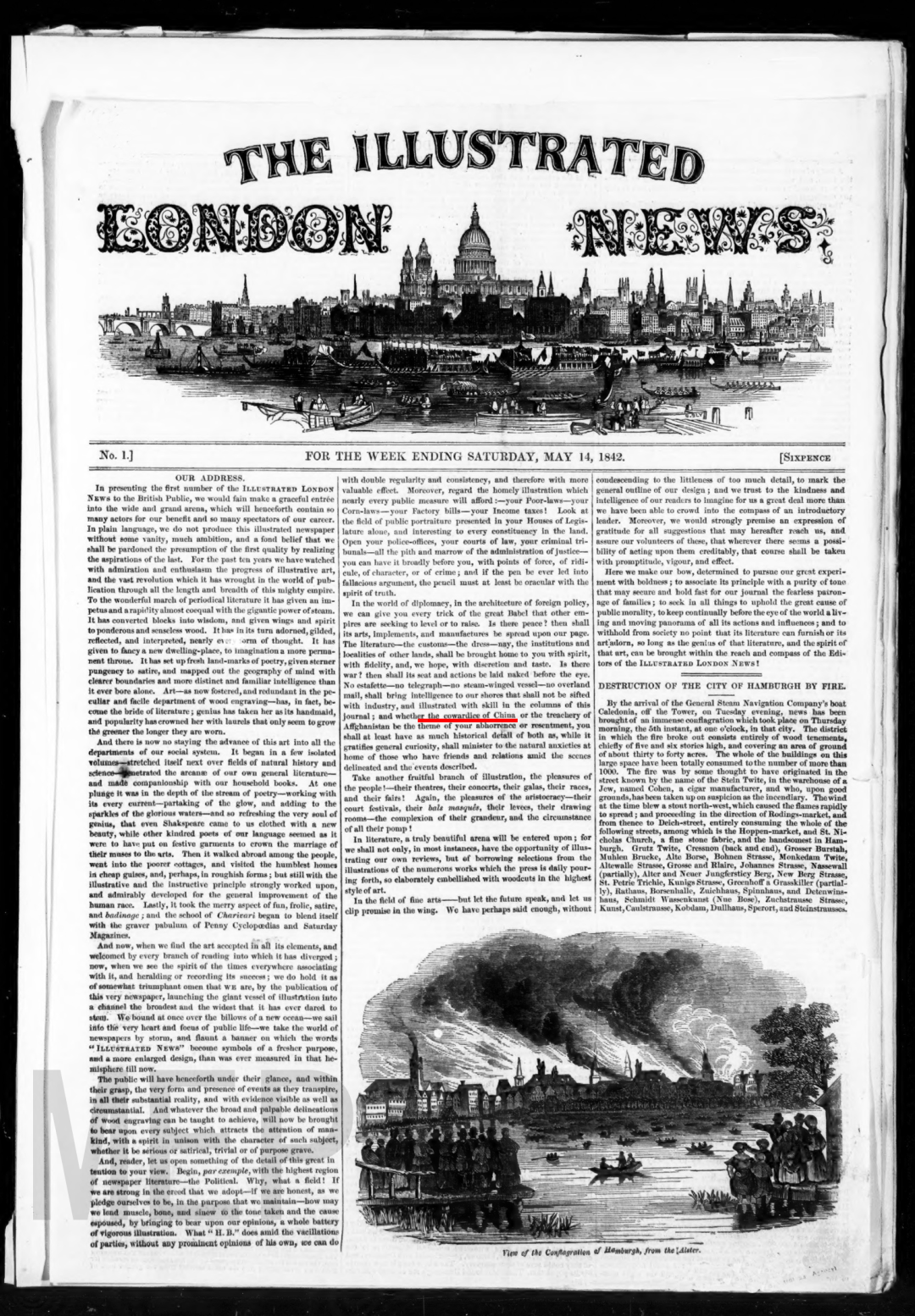
《倫敦新聞畫報(bào)》創(chuàng)刊號(hào)第1版,1842年5月14日
(報(bào)道首次提及“中國(guó)”一詞)
? ? ? ? ?全書(shū)計(jì)5章,第一章“時(shí)代變局下的統(tǒng)治者”、第二章“影響國(guó)運(yùn)的權(quán)臣大吏”,分別編選關(guān)于晚清君、臣的相關(guān)報(bào)道;第三章“外患內(nèi)亂下的九州”以戰(zhàn)爭(zhēng)為主線記述晚清重大事件,展示了一些以往鮮為人知的歷史畫面;第四章“山河破碎的人間萬(wàn)象”主要聚焦社會(huì)層面,反映動(dòng)蕩年代的眾生百態(tài)及社會(huì)斷面;第五章“東方與西方的碰撞”以小見(jiàn)大,通過(guò)西人對(duì)日常生活細(xì)節(jié)的報(bào)道,反映東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及晚清中國(guó)的演變。
? ? ?全書(shū)內(nèi)容涉及政治、軍事、外交、經(jīng)濟(jì)、社會(huì)、文化等,人物從君主、權(quán)臣到普通民眾,5章是一個(gè)整體,前后呼應(yīng)、連貫,勾勒出晚清史的基本線索和特征,避免了內(nèi)容的“碎片化”和條塊分割。
? ? 《倫敦新聞畫報(bào)》的報(bào)道出于西人筆下,西人對(duì)中國(guó)歷史文化的隔膜、報(bào)道采訪客觀存在的難度,導(dǎo)致其報(bào)道不免摻雜道聽(tīng)途說(shuō)和臆想成分,存在史實(shí)錯(cuò)誤。譬如,畫報(bào)1908年的報(bào)道說(shuō)光緒帝不到30歲就去世、傳位9歲的溥儀(20頁(yè)),實(shí)際上光緒帝38歲去世、溥儀3歲繼位;又說(shuō)兩廣總督葉名琛處決了在廣州“作亂”的太平軍十幾萬(wàn)人(38頁(yè)),事實(shí)上,舉兵圍攻廣州的是天地會(huì)武裝,自稱“洪兵”或“紅兵”,今人稱之為“紅巾軍”。編者逐一訂正了此類錯(cuò)誤。
? ? ? 全書(shū)涉及內(nèi)容甚廣,編者在解讀時(shí),參閱了大量包括清宮檔案在內(nèi)的原始文獻(xiàn),參考了相關(guān)研究著述,敘述準(zhǔn)確,文字簡(jiǎn)練。書(shū)中加了不少注釋,并擇要開(kāi)列了反映學(xué)界最新研究成果的相關(guān)著述及資料匯編,約有百余部(篇),增強(qiáng)了該書(shū)的權(quán)威性。譬如,關(guān)于1857年發(fā)生在香港的“毒面包案”,編者結(jié)合圖像,指出裕盛辦館是當(dāng)時(shí)香港唯一供應(yīng)西式面包的辦館,并解釋了“辦館”一詞的特定含義。
? ? ? 該書(shū)所選取的不少報(bào)道和圖像具有重要價(jià)值,豐富、深化了我們對(duì)相關(guān)歷史的認(rèn)識(shí)。例如,1843年3月3日,裝載鴉片戰(zhàn)爭(zhēng)中國(guó)賠款、計(jì)20余噸中國(guó)銀錠的5輛馬車,在英國(guó)士兵押送下,從南安普敦火車站送至英國(guó)鑄幣廠,將被重新鑄造;插圖中的兩位中國(guó)官員則是負(fù)責(zé)移交賠款的專使(30頁(yè))。這一幕令人噓唏不已。
? ? ?再如,1859年,該畫報(bào)特約畫家兼記者私自走訪我國(guó)臺(tái)灣島西南海岸,贊嘆“這是一個(gè)美麗的地方”,山脈連綿,古樹(shù)蔥蘢,民人淳樸友善。他受到當(dāng)?shù)毓倜窨畲穱L了蘸糖鳳梨,喝茶、嚼檳榔,雖不懂閩南方言,用紙筆一樣溝通,不由得感嘆“因?yàn)檎麄€(gè)帝國(guó)使用統(tǒng)一的漢字”(162頁(yè))。
? ? ? 該畫報(bào)對(duì)中國(guó)的報(bào)道是多元的,其中不乏相對(duì)正面的報(bào)道。譬如,談到已故前駐英公使曾紀(jì)澤,對(duì)其贊譽(yù)有加,認(rèn)為他是“杰出的中國(guó)政治家和外交家”,“才華卓著、赫赫有功”(54頁(yè))。
? ? ??再如,稱贊1851年在倫敦萬(wàn)國(guó)博覽會(huì)中國(guó)館的一個(gè)中國(guó)家庭的表現(xiàn),內(nèi)云:“這一家庭組合真是可嘉可贊,容貌裝扮鮮明而獨(dú)特,凸顯出一個(gè)中國(guó)家庭的原生風(fēng)貌。他們的言行舉止表露出謙恭和親和,十分得體。這一家人一團(tuán)和氣,相互照應(yīng),這給觀眾留下了美好印象。”(192頁(yè))
? ? ? 1859年,該畫報(bào)畫家在香港周邊海灣的山區(qū)旅行,在村民家用餐,中國(guó)人友善、好客的一面給其留下深刻印象。據(jù)載,“在這些村莊里一派自由、平等和博愛(ài)的氛圍。每個(gè)人都悠然地抽著煙、喝著茶”(213頁(yè))。
? ? ? 談到戰(zhàn)爭(zhēng),該畫報(bào)承認(rèn)中國(guó)軍隊(duì)有英勇的一面。譬如,記述1842年4月清軍在寧波抵御英軍,一次陣亡六七百人,“他們的戰(zhàn)斗比以往任何時(shí)候都更加堅(jiān)定”(75頁(yè))。
? ? ? 關(guān)于西方列強(qiáng)侵華造成的劫難,該畫報(bào)也有報(bào)道。譬如,1858年8月14日的一篇配圖報(bào)道標(biāo)題為“一場(chǎng)野蠻的劫掠后的廣州鬧市”,描述英法聯(lián)軍攻占廣州城造成的荒涼場(chǎng)景(86—87頁(yè))。畫報(bào)還從入侵者視角記述了廣州軍民抗擊聯(lián)軍的行動(dòng),并轉(zhuǎn)引一位英國(guó)士兵的家書(shū),講述軍營(yíng)日益彌漫的厭戰(zhàn)情緒:不分晝夜、無(wú)休止的戰(zhàn)斗使人“感到疲憊不堪”,心生“厭惡和疲憊”,內(nèi)心祈求和傷員一樣,下次寫信時(shí)“同樣在回家路上”(80—81頁(yè))。
? ? ??不言而喻,該畫報(bào)是英國(guó)喉舌,其主旨是為英國(guó)政府的侵華政策辯解,以獲取本國(guó)輿論支持,所持歷史觀本質(zhì)上是錯(cuò)誤的,雖有極少持平之論,但總體上充斥著居高臨下心態(tài)、狹隘偏見(jiàn)和蠻橫。在他們筆下,中國(guó)社會(huì)專制愚昧,似一潭死水;中國(guó)人拖辮子、吸鴉片、女子裹小腳,暮氣沉沉。譬如,據(jù)報(bào)道,1857年春從錫蘭開(kāi)往香港的客輪頭等艙乘客中有一中國(guó)人,用西餐、有派頭,但無(wú)人理會(huì),“待他比狗還差,因?yàn)樗侵袊?guó)人,而英國(guó)人正在廣州開(kāi)戰(zhàn)”(143頁(yè))。該畫報(bào)“西方中心論”觀點(diǎn)俯拾即是,宣稱“蒸汽船不僅給中國(guó)帶來(lái)了商品,還有人、思想、機(jī)器以及與現(xiàn)代文明有關(guān)的一切”(11頁(yè)),妄言只有西方文明才能拯救落后的東方世界,其潛臺(tái)詞是中國(guó)理應(yīng)成為西方附庸;動(dòng)輒強(qiáng)詞奪理顛倒黑白,大肆渲染中國(guó)人如何“野蠻殺戮”外國(guó)人,以爭(zhēng)取西方世界的輿論支持,為侵華戰(zhàn)爭(zhēng)的“正義性”尋找理由。
? ? ? 該書(shū)編者在“導(dǎo)言”鄭重提醒讀者:“在閱讀本書(shū)時(shí)要抱著審視的目光看待這些圖像,圖像的內(nèi)涵與圖像本身同樣值得深思。”編者在正文中不時(shí)就此加以剖析,言簡(jiǎn)意賅直指要害。
? ? ? 例如,畫報(bào)記述1858年一名被俘的英軍士兵獲釋歸來(lái),自稱“好吃好喝,未受虐待”,認(rèn)為這“說(shuō)明當(dāng)?shù)刂袊?guó)人已懂得‘文明戰(zhàn)爭(zhēng)’的性質(zhì)”。編者分析說(shuō):“英國(guó)人將自己發(fā)動(dòng)的入侵他國(guó)的戰(zhàn)爭(zhēng)稱為‘文明戰(zhàn)爭(zhēng)’,這恐怕只能是盎格魯—撒克遜的文明邏輯了。”(87頁(yè))
? ? ? 再如,該畫報(bào)報(bào)道《中英天津條約》簽訂一事,大言不慚地認(rèn)為這“不僅是結(jié)束數(shù)月的流血與苦難,而且很可能引領(lǐng)這個(gè)獨(dú)特而美好的帝國(guó)的未來(lái)進(jìn)入更光明的時(shí)期”。編者一針見(jiàn)血指出:“英、法、俄、美等列強(qiáng)逼迫清政府簽訂《天津條約》,這種喪權(quán)辱國(guó)的不平等條約帶給中國(guó)的絕不是光明,而是更苦難的黑暗!”(41頁(yè))
? ? ? 又如,該畫報(bào)1857年將英國(guó)駐華公使約翰·包令描述為“中國(guó)的朋友和愛(ài)好和平的人”,其堅(jiān)持對(duì)華動(dòng)武開(kāi)戰(zhàn)是“不情愿的”,是“被迫采取艱難而特殊的立場(chǎng)”。編者反駁道:“事實(shí)上武力威嚇與脅迫自始至終是英國(guó)在中國(guó)攫取利益的必選手段。”(83頁(yè))
? ? ??總之,《〈倫敦新聞畫報(bào)〉中的中國(guó)人:1842—1912》一書(shū)具有獨(dú)特價(jià)值。借此回首110年前的這段歷史,對(duì)于我們樹(shù)立正確歷史觀、堅(jiān)定不移地走自己選擇的發(fā)展道路大有裨益。